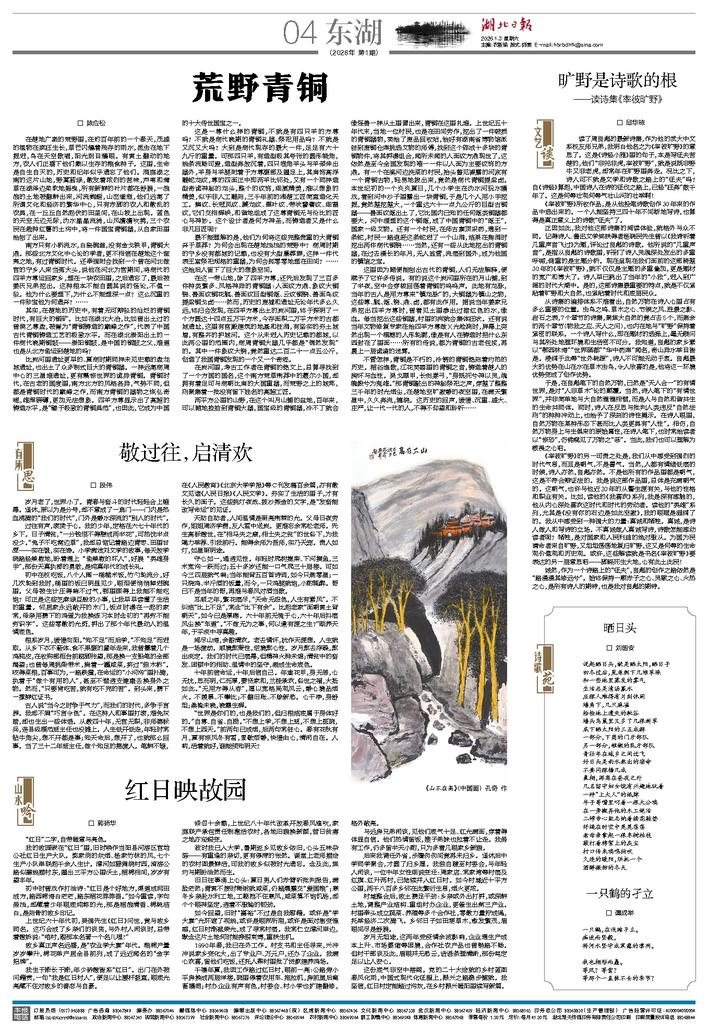□ 郭扬华
“红日”二字,自带暖意与亮色。
我的故园嵌在“红日”里,旧时唤作当阳县河溶区官垱公社红日生产大队。郭家岗的炊烟、杨家竹林的风,七个生产小队串联起千余人生计。漳河如碧绸绕村西,淯溶公路似墨线描村东,圈出三平方公里沃土,稻棉相间,岁岁有望丰年。
初中时曾戏作打油诗:“红日是个好地方,渠道成网田成方,路西棉海白茫茫,路东稻花阵阵香。”如今重读,字句虽浅,却藏着少年眼底纯粹的光,那是稻浪清香、棉桃洁白,是刻骨的故乡印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强先生《红日》问世,竟与故乡同名。这巧合成了乡亲们的谈资,与外村人闲谈时,总带着傲娇说:“咱村,跟那本名著一个名儿哩!”
故乡真正声名远播,是“农业学大寨”年代。粮棉产量岁岁攀升,棉花单产居全县前列,成了远近闻名的“金字招牌”。
我生于斯长于斯,年少骄傲皆系“红日”。出门在外被问籍贯,一句“我是红日村人”,便足以让腰杆挺直,眼底光亮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与自豪。
倏忽十余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遍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各地旧貌换新颜,昔日贫瘠之地亦迎蜕变。
彼时我已入大学,暑期返乡见故乡依旧,心头五味杂陈——有重逢的亲切,更有停滞的怅然。课堂上老师描绘的农村图景鲜活,可我的故乡似被时光遗忘。念及此,焦灼与期盼油然而生。
旧日往事涌上心头:夏日男人们赤臂听批判报告,满脸茫然;青黄不接时稀粥就咸菜,仍踏晨露交“爱国粮”;寒冬乡亲赴水利工地,工棚挡不住寒风,咸菜填不饱饥肠,却个个眼神坚定,透着不服输的韧劲。
如今回望,旧时“富裕”不过是自我慰藉。或许是“学大寨”光环遮了视线,或许是眼界所限,或许是面对剧变惶惑,红日村渐褪荣光,成了寻常村落。我常伫立漳河岸边,默念这片土地何时能挣脱束缚,重获生机。
1990年春,我已在外工作。村支书和主任寻来,兴冲冲说家乡变化大,出了专业户、万元户,还办了企业。我满心欢喜,留他们吃饭,还托人帮村里批了贷款建养鸡场。
千禧年夏,我因工作路过红日村,眼前一亮:公路旁小平房换成两层洋楼,院里停着农用车、拖拉机,房前屋后禽畜嬉闹;村办企业有声有色,村委会、村小学也扩建翻修,格外敞亮。
与远房兄弟闲谈,见他们底气十足、红光满面,穿着得体显自信。他们热情留饭,嫂子弟妹也拉着不让走。我虽有工作,仍多留半天小酌,只为多看几眼家乡新貌。
后来我调任外省,步履匆匆间竟再未归乡。退休后中学同学聚会,才圆了归乡愿。我独自踱至村委会,与年轻人闲谈,一位中年女性细说变迁:周家店、常家湾等村落及红旗、红升两村,已陆续并入红日村。如今村域近十平方公里,两千八百多乡邻在此繁衍生息,烟火更浓。
村域整合后,故土攒足干劲:乡亲或外出打拼,或深耕土地,调整产业结构、重组村办企业,更催生出第三产业。村里牵头成立蔬菜、养殖等多个合作社,零散力量拧成绳,托举经济二次腾飞。乡邻日子如田埂草木,愈发繁茂,眉眼间尽是舒展。
岁月无坦途,这两年受疫情余波影响,企业遇生产成本上升、市场萎缩等困境,合作社农产品也曾销路不畅。但村干部谈及此,眉眼并无愁云,话语条理清晰,那份笃定足以让人安心。
这份底气非空中楼阁。党的二十大绘就的乡村蓝图春风化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振兴之路稳步铺就。我坚信,红日村定能踏过沟坎,在乡村振兴暖阳里续写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