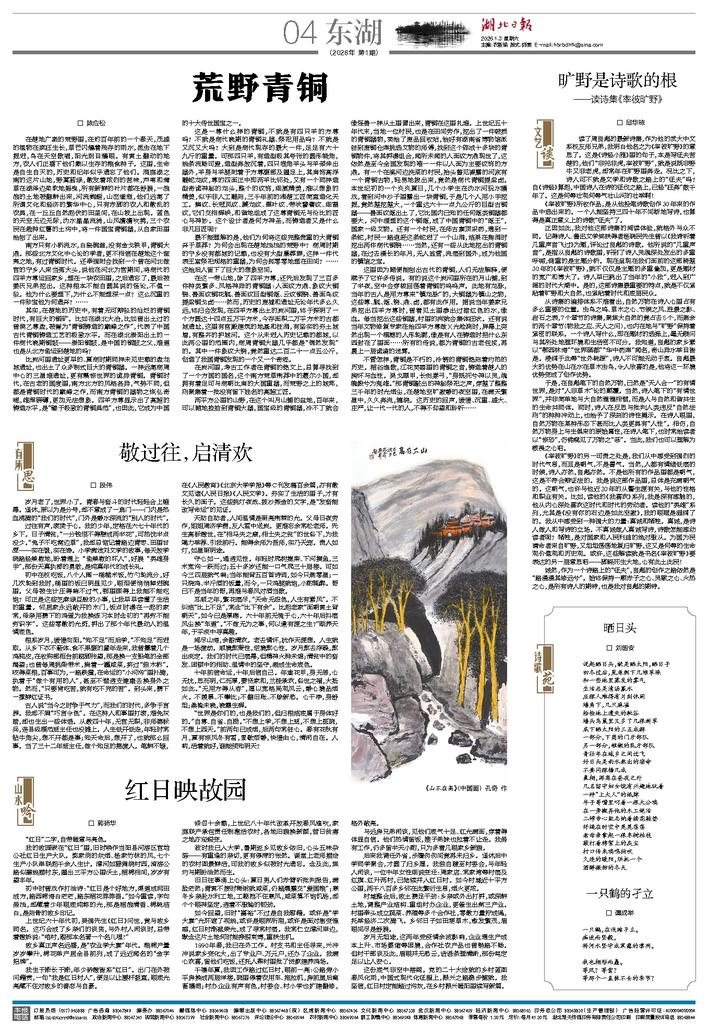□ 段伟
岁月老了,世界小了。青春与奋斗的时代轻轻合上帷幕。退休,原以为是分号,却不意成了一扇门——门内是热血沸腾的“我们的时代”,门外是静水深流的“别人的时代”。
过往有声,滚烫于心。我的少年,定格在六七十年代的乡下。日子清贫,“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可热忱半点没少。“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却总惦记着路边青枣、田里甘蔗——实在饿,实在馋。小学痴迷刘文学的故事,每天放学绕路经辣椒地,盼着遇上 “偷辣椒的坏人”,好展 “英雄身手”,那份天真执拗的勇敢,是纯真年代的成长礼。
初中在校吃饭,八个人围一桶糙米饭,竹勺轮流分,好几次轮到我时,桶里的饭已明显见少,眼泪便悄悄掉进碗里。父母被生计压得喘不过气,哪里顾得上我能不能吃饱?可正是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让我早早读懂了生活的重量。邻居家永远敞开的木门,饭点时凑在一起的家常,母亲用攒下的鸡蛋为我换练习本时念叨的“再穷不能穷识字”。这些零散的光斑,拼出了那个年代最动人的温情底色。
根系岁月,缓慢向阳。“知不足”而后学,“不知足”而进取。从乡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童年走来,我曾攥着几个鸡肫皮,在收购部柜台前踮脚张望,那是换一支铅笔的全部渴望;也曾每周挑柴带米,揣着一罐咸菜,挤过“独木桥”。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一路跌撞,在命运的“小河沟”里扑腾,执着于“做个有用的人”,甚至不惜透支健康去换身外之物。然而,“只要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到头来,攒下一摞鲜红证书。
古人说“当今之时争于气力”,而我们的时代,多争于言辞。我却不屑“巧言令色”。在这种人和事里打滚,难免灰暗,却也生出一些体悟。从教四十年,无官无职,非师德标兵,连县级模范班主任也没摊上。人生低开低走,年轻时常钻牛角尖,想不开都是事;知天命后,想开了,也就那么回事。当了三十二年班主任,做个知足的摆渡人。笔耕不辍,在《人民教育》《北京大学学报》等C刊发稿百余篇,亦有散文见诸《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夯实了生活的里子,才有长久的面子。这些挑灯夜战、披沙拣金的文字,是“发奋能改写命运”的见证。
天助自助者,人间温情是照亮荆棘的光。父母日夜劳作,姐姐周济学费,友人雪中送炭。更难忘余常松老师。先生高标傲世,在“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世俗下,为我竭力举荐、引我前行。能得余师为吾师,实乃天宠。贵人如灯,如星照明途。
守心如一,通透见性。年轻时爬树摘梨、下河摸鱼,三米宽沟一跃而过;五十多岁还能一口气爬三十层楼。可如今三四层就气喘;当年能背五百首诗词,如今只剩零星;一只烧鸡、半斤酒的饭量,而今,一只鸡腿就饱,小酌辄醉。哥已不是当年的哥,再难与春风对酒当歌。
耳顺之年,繁花落尽,“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不纠结“比上不足”,常念“比下有余”。比起老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已是厚赐。六十年前无愧于心,六十年后抖落风尘换“车道”。“不做无为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颐养天年,于平淡中寻真趣。
阅尽山海,余韵清欢。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人生就是一场渡劫。顺境熬秉性,逆境熬心性。岁月熬去浮躁,熬出淡定。我们的时代已落幕,但精神火种未熄;清贫中的奋发、困顿中的相助、温情中的坚守,凝成生命底色。
十年前信命运,十年后信自己。年逾花甲,身无恙,心无忧,思而明,仁而厚,妻贤家和,兰桂承欢,俗世之福,大抵如此。“无用方得从容”,愿以宽格局观风云,静心境品烟火。不羡慕、不攀比;不翻旧账、不赊新愁。心干净,身舒坦;桑榆未晚,晚霞生辉。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属于身体好的。”自尊、自省、自励。“不想上学,不想上班,不想上医院,不想上西天。”前两句已成烟,后两句常驻心。春有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累歇烦静,快慢由心,清闲自在。人呐,活着就好,谁能预知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