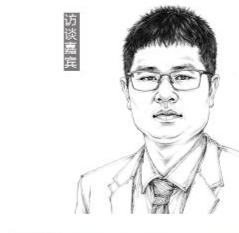阅读提要
一个区域要出现科技初创企业,就要构建适合科技初创企业生长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容性和增强各种要素供给,如人才、资本供给等。
很多科技创新要发展起来,才能看到规范的必要性,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就匆忙地去限制企业发展,这不利于建立科技产业优势。
创新是企业的事,如果企业创新出现了障碍,那么此时就需要地方作为;如果企业创新没有出现障碍,那么政府就应该退避三舍。
只有“放”才能活,只有“让”才能飞
湖北日报记者:“杭州六小龙”的出现,给各地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盘和林:在科技革新的时代浪潮中,“杭州六小龙”——游戏科学、深度求索(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群核科技,宛如闪耀的新星,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脑科学等前沿领域披荆斩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它们不仅彰显了中国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也为杭州这座“数字之城”注入了新活力。
杭州给予各地的启示,可以从创立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的条件出发。对于创业者来讲,最需要的就是资本、人才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资本方面,杭州地处江浙沪,民营经济发达带来的好处,就是民营资本也随之壮大。民营企业家集合一些资金,成立了各类私募投资基金,如深度探索公司的底气就来自幻方量化私募基金。可以说,如果背后没有发达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杭州六小龙”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发展底气。
人才方面,杭州的各大高校构成了杭州人才供给的基础。当然,城市要留住毕业生,必须有与专业匹配的就业,而杭州“电商之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正是因为阿里等企业的存在,杭州留住了大量互联网科技领域的人才;正是因为这些企业人才的高流动性,大量人才走出去了,在杭州进行二次就业和创业;也正是围绕这群人,杭州有了互联网科技的技术交流圈子,交流多了,各种想法和创意就会不断涌现。
营商环境是杭州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杭州对于所有民营企业都有很好的包容性。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对外开放“桥头堡”,有着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的优良传统。和其他地区不同,杭州的国有经济相对薄弱,对民营经济的依赖性很强,当地善于向民企让步、让路。比如杭州西湖不卖门票,客观上就是给民营企业让路;比如杭州电商的发展壮大,是杭州包容、宽容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结论就是:只有“放”才能活,只有“让”才能飞。这个“让”,是政府和国企给民企让路,帮民企省事、平事。
总之,“杭州六小龙”给各地发展带来的启示在于:一个区域要出现科技初创企业,就要构建适合科技初创企业生长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容性和增强各种要素供给,如人才、资本供给等。只有制度供给、人才供给、资本供给都跟上了,区域内的科创企业才能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是大势所趋
湖北日报记者:从湖北来看,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面临着怎样的竞争态势?
盘和林:湖北制造业偏重,经济底色是好的,尤其是武汉非常注重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通信制造、汽车制造。对于湖北制造业来说,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能提质增效、降本增效,也能缔造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缔造新经济来驱动发展。更加重要的是,未来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是大势所趋。
对于湖北来说,应该先激活人工智能产业,吸引外部的人工智能企业,鼓励本土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展。有了规模足够的人工智能产业,湖北才能更快地推进域内企业和政府向智能化转型。与此同时,湖北也要发挥自身在制造业上的优势,争取在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算力依然是瓶颈,湖北需要向算力全产业链做拓展,比如科技壁垒最高的是芯片,而相对壁垒低一点的是云计算。
少给企业找事,多给企业“平事”
湖北日报记者:新春开工以来,各省份都表达了对新科技的拥抱,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该有怎样的作为?又要避免哪些问题?
盘和林:从根本上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只是喊口号,而是要给予企业发展更多支持。一方面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各地财力不同,给予企业真金白银支持的力度不同,靠补贴规模去内卷没有太大意义,但至少不应该让本地政府在这方面落后太多;另一方面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要素供给来支持企业投资,鼓励企业创新。其中营商环境的支持主要体现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就是少给企业找事,多给企业“平事”,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增加要素供给方面,湖北是科教大省,人才供给不弱于其他地区,关键是要把人才资源留在武汉,并逐渐形成一个人才交流的圈子。当然,承载人才最主要的手段是就业,武汉的优势在于科研院所较多,科研机构可以通过扩容承载更多人才。除此之外,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建立一套高效的人才选拔体系,把人才优势真正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在资本供给方面,湖北相对缺少具备资本规模的民营资本,政府在科技投资上可以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比如政府主导的创投母基金的方式,政府领投,民营资本跟进,由专业风险投资机构主导,来筛选值得投资的初创公司。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壮大企业,需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需要增强资本和人才供给。这些之外,还需要在创新上给予激励,激励的手段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揭榜挂帅,给予一个研发目标,研究项目向企业招标;比如可以是产学研融合发展,让科研机构和企业一同发力,政府搭台,科技机构和企业唱戏;比如可以是专利产权保护;比如可以是更高的科技前沿包容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避免过多的管控和政府干预,要先立后破,而非先破后立。很多科技创新要发展起来,才能看到规范的必要性,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就匆忙地去限制企业发展,这不利于建立科技产业优势。飞梭的发明人约翰·凯伊,其发明飞梭后想要向英国国王申请专利的时候却被拒绝了,理由是飞梭提高了效率,但减少了就业。从现实来看,推动自动驾驶发展,不能因噎废食,要抓住科技风口,助力科技发展,等科技应用成熟之后,再去考虑社会整体效益,并作出相应的规范。
政府助力企业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湖北日报记者:企业创新与地方作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盘和林:创新是企业的事,如果企业创新出现了障碍,那么此时就需要地方作为,比如企业找不到人才、找不到资本、找不到专利,政府可以成为桥梁。除此之外,如果企业创新没有出现障碍,那么政府就应该退避三舍,既要防止政府更多地“光顾”“访问”企业,也要防止政府下辖的国有企业过度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为企业创新提供助力。这种助力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撬动社会资本对科技企业进行投资,这是一种母基金的模式;一种方式是政府通过购买采购的方式来支持科技初创企业,将科技初创企业的产品率先用在公共服务领域。这样,既能够升级公共产品,也能够促进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
总之,在创新和地方作为之间,地方应该做好一个发展的促进者,要从创新企业的体感出发,少添麻烦多帮忙。这方面杭州是有借鉴经验的,浙江曾推出“最多跑一次”。后来,“最多跑一次”变成了“一网通办”,办事员平时不会去找企业,只在企业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针对民企的服务细节和政府部门的感同身受是地方最需要的。
生产力之“新”不能脱离本地产业生态
湖北日报记者:如何从源头上提升生产力之“新”?
盘和林:首先,不要苛求,要因地制宜。要从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有多大的碗就盛多少饭。和长三角、珠三角竞争,湖北能拼的,是人才,是创意,是营商环境,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潜在需求。湖北科研高校多、制造企业多,如发展汽车产业,引入自动驾驶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而对自动驾驶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乐见其成,保护好科技苗子,让其成长起来。所谓创新,要因地制宜,脱离了本地的产业生态,那么“新”就无从谈起。
其次,要真金白银投入。投入多少才能产出多少。投入产出的效率是可以优化的,但没有投入必然没有产出,而在投入上,政府先要克服对科技原创、长期科技烧钱的投资恐惧,如果政府对科技没有信心,怎么指望民营资本对科技企业有信心呢?
再者,要完善激励机制。政府投资科创企业,可能会成功,可能会失败,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过程是秉持科学客观的态度。民营企业和资本的激励机制是明确的,但国企和政府的激励机制要完善,要激励相容。
最后,要释放政府手头的资产。具体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释放政府的科技专利资产。比如美国历史上就有《拜杜法案》,目的是将美国政府手上的科研技术全部卖给私人企业,诸如高通以前的技术叫CDMA,这项技术就是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声呐探测技术,诸如ASML紫光激光器最早就来自美国星球大战的科研成果。企业才是创新的最好载体,将专利和人才放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手上,既鼓励了民企,也让人才和专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