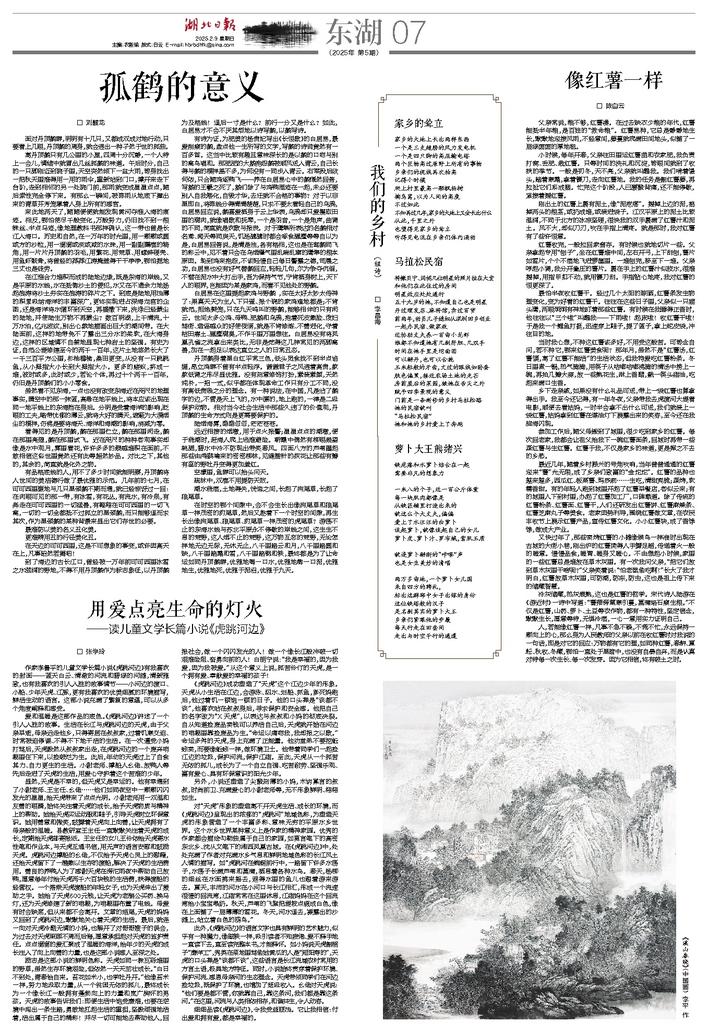□ 陈白云
父亲常说,粮不够,红薯凑。在过去缺衣少粮的年代,红薯能抵半年粮,是百姓的“救命粮”。红薯易种,它总是静静地生长,默默地迎接风雨,不经意间,藤蔓就爬满田间地头,似铺了一层绿茵茵的厚地毯。
小时候,每年开春,父亲往田里运红薯苗和农家肥,我负责打窝、丢肥、栽红薯。只等时间的洗礼和沉淀,转眼间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一般是初冬,天不亮,父亲就叫醒我。我们啃着馒头,踏着寒霜,拿着镰刀,走向红薯地。我的任务是割红薯藤,再拉扯它们系成捆。忙完这个阶段,人已腰酸背痛,还不能停歇,紧接着搓红薯。
刚出土的红薯上裹有泥土,像“泥疙瘩”。搓掉上边的泥,掐掉两头的根茎,或扔成堆,或装进袋子。江汉平原上的泥土比较温润,不同于北方的冰凉坚硬,很快我的双手裹满了红薯汁和泥土。风不大,却似刀刃,吹在手指上清疼。就是那时,我对红薯有了些许恨意。
红薯收完,一般拉回家窖存。有时候也就地切片一些。父亲拿起专用“刨子”,坐在红薯堆中间,左右开弓,上下刮刨,薯片如雪片,个个不落地飞进箩筐里。一堆刨完,移至下一堆。父亲哼起小调,我分开叠压的薯片。裹在手上的红薯汁似胶水,很难搓掉,用指甲扣不动,就用镰刀刮。手指钻心地疼,我对红薯的恨更深了。
最怕半夜收红薯干。经过几个太阳的晾晒,红薯条发生物理变化,变为好看的红薯干。往往在这些日子里,父亲似一只猫头鹰,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那些红薯。有时候在我睡得正香时,他往往以“三个啦”叫醒我——下雨啦!起床啦!收红薯干啦!于是我一个鲤鱼打挺,迅速穿上鞋子,提了篮子,拿上蛇皮袋,冲往目的地。
当时我心想,不种这红薯该多好,不用受这般苦。可转念自问,若不种它,哪来红薯美食呢?那年月,虽然不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生活状态,但我特爱吃红薯粉条。冬日里煮一锅,热气腾腾,用筷子从咕嘟咕嘟沸腾的清汤中捞上一碗,再拍几瓣大蒜,放一些熟花生,淋上香醋,戳一筷头猪油,吃起来满口生香。
乡下走亲戚,如果没有什么礼品可送,带上一袋红薯也算拿得出手。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冬夜,父亲带我去虎渡河大堤看电影,顺便去看姑妈,一时半会拿不出什么可送,我们就装上一袋红薯,姑妈拿到红薯在煤油灯下展露出来的笑容,至今还在我脑海闪现。
参加工作后,随父母搬到了城里,很少吃到家乡的红薯。每次回老家,我都会让祖父给我下一碗红薯面条,回城时再带一些蒸红薯与生红薯。红薯于我,不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最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当年普普通通的红薯迎来“薯”光无限,成了乡亲们致富的“金坨坨”。红薯的品种也越来越多,西瓜红、板栗薯、玛莎莉……生吃,清甜爽脆;蒸烤,软糯香甜。有的年轻人跑到城里开起了红薯早餐店,客似云来;有的城里人下到村里,办起了红薯加工厂,口碑载道。除了传统的红薯粉条、红薯面、红薯干,人们还研发出红薯饼、红薯麻辣条、红薯芝麻丸子等美食。老家因势利导,围绕红薯做文章,在农民丰收节上展示红薯产品,宣传红薯文化。小小红薯块,成了香饽饽,做成大产业。
又快过年了,那些卖烤红薯的小摊像候鸟一样准时出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刚出炉的红薯烫得人手舞足蹈,传递着火一般的暖意。慢慢品食,暖胃、暖身又暖心。不由想起小时候,家里的一些红薯总是堆放在草木灰里。有一次我问父亲,“把它们放到草木灰里干啥呢?”父亲笑着说:“怕老鼠偷吃啊!”长大了我才明白,红薯放草木灰里,可防潮,防冻,防虫,这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储藏智慧。
冷灰储藏,热灰煨熟,这也是红薯的哲学。宋代诗人陆游在《游近村》一诗中写道:“薯蓣傍篱寒引蔓,菖蒲络石瘦生根。”不仅是红薯,山药、萝卜、土豆等农作物,都有一种特性,坚定信念,默默生长,愿意等待,无惧冷落,一心一意用实力证明自己。
人,若能像红薯一样,凡事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永远保持一颗向上的心,那么身为人民教师的父亲以前在收红薯时对我说的一句话,即是对它的回应:万物都有它的理,如同种红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哪怕一直处于黑暗中,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认真对待每一次生长、每一次发芽。因为它相信,终有破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