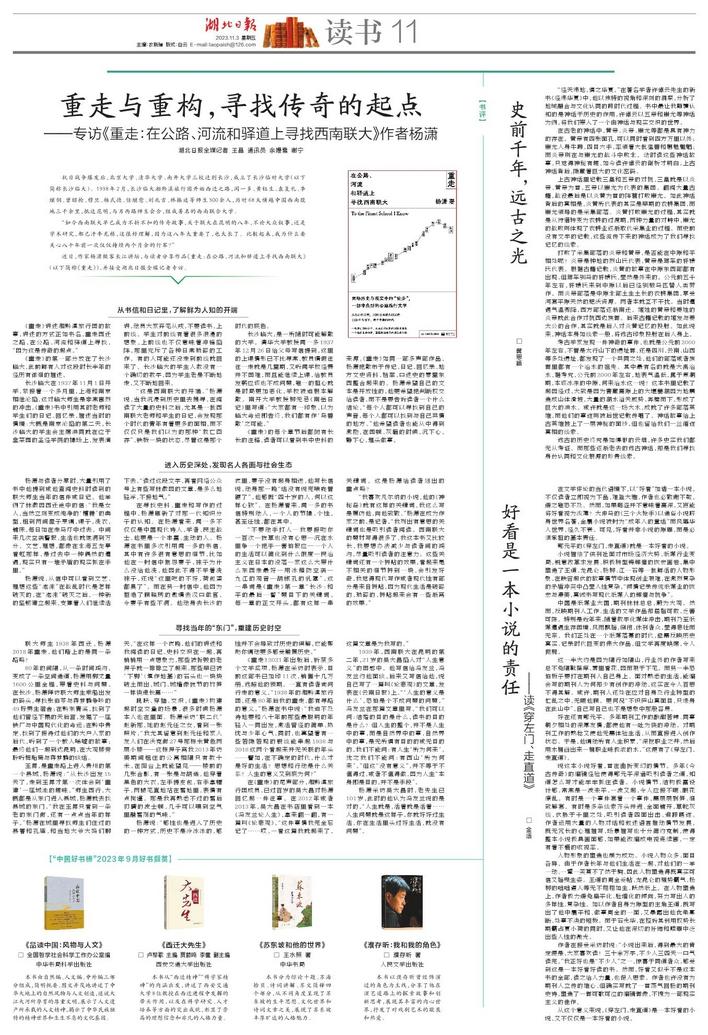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余嫚雪 谢宁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到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长沙临大)。1938年2月,长沙临大湘黔滇旅行团开始西迁之路,闻一多、黄钰生、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穆旦、杨式德、任继愈、刘兆吉、林振述等师生300余人,历时68天横越中国西南腹地三千余里,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如今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关于联大在昆明的八年,不论大众叙事,还是学术研究,都已汗牛充栋,这很好理解,因为这八年太重要了,也太长了。比较起来,我为什么要关心八十年前一次仅仅持续两个月余的行军?”
近日,作家杨潇做客长江讲坛,与读者分享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并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
从书信和日记里,了解鲜为人知的开端
《重走》讲述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讲述的方式正如书名,重走西迁之路,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因为这是传奇的起点。”
《重走》的第一部分放在了长沙临大,此前鲜有人对这段时长半年的经历有详细的描述。
长沙临大在1937年11月1日开学,紧接着一个多月里,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这对临大师生是非常剧烈的冲击。《重走》书中引用其时老师和学生们的日记、回忆录,描述当时的情境:大概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长沙临大的学生会主席洪同就在位于韭菜园的圣经学院的操场上,发表演讲,动员大家弃笔从戎,不要读书,上前线。学生对前线有着很多浪漫的想象,上前线也不仅意味着冲锋陷阵,那里充斥了各种日常琐碎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还没走到前线就回来了。长沙临大的学生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学生老是不断地走,又不断地回来。
“这是西南联大的开端。”杨潇说,当我沉浸到历史里去搜寻,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之后,尤其是一批西南联大老师和学生的日记,会发现那个时代的青年有着更多的面相,而不仅仅只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救亡图存”、铁板一块的状态,尽管这是那个时代的底色。
长沙临大,是一所随时可能解散的大学。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1937年12月26日给父母写信提到,这里的上课情形已不比寻常,教员请假往往一走就是几星期,又听闻学校经费并不困难,而且能继续上课,给教员发薪应该也不成问题,唯一的担心就是时局更加恶化,学校被迫根本解散。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南岳日记》里写道:“大家都有一印象,以为临大命运即告终,我们都有作‘鸟兽散’之可能。”
《重走》的每个章节后都附有长长的注释,读者可以看到书中史料的来源。《重走》如同一部多声部作品,杨潇把散布于传记、日记、回忆录、地方文史资料、档案、口述史的零星东西整合起来的。杨潇希望自己的文本是开放性的,他更希望把判断权交给读者,而不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什么结论,“每个人都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与自己共情的地方。”他希望读者也能从中得到激励,在困顿、灰暗的时候,沉下心,静下心,埋头做事。
进入历史深处,发现名人各面与社会生态
杨潇与读者分享时,大量引用了书中他提到或他查阅史料时读到的联大师生当年的信件或日记。他举例了林徽因西迁途中的信:“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五龙亭看虹那样,是过去中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
杨潇说,从信中可以看到文艺、理想这些“泡沫”在战乱时代是怎样破灭的,在“泡沫”破灭之后,一种新的坚韧建立起来,支撑着人们继续活下去。“读过这段文字,再看网络公众号上有些写林徽因的文章,是多么地轻浮,不接地气。”
在寻找史料、重走和写作的过程中,杨潇刷新了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认知。在杨潇看来,闻一多不仅仅是中国现代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他更是一个丰富、生动的人。杨潇在书里多次引用闻一多的书信,其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他在一封信中抱怨妻子,袜子为什么没给他洗,他因此不得不学着洗袜子,还说“这里吃的不好,荷包蛋都臭了”。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因为拒绝了顾毓琇的邀请去汉口做官,令妻子有些不满。他动身去长沙的夜里,妻子没有起身相送,他写长信说,动身那一晚“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他感慨“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在杨潇看来,闻一多的书信特别动人,一个人的节操、个性,甚至任性,都在其中。
“不要动手打人—我要接吻你一百次—拔草也没有心思—沉在水里争一个把手—害怕报应—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民治主义在日本的没落—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最好—用冰箱防空袭—九江的观音—胡椒孔的乳罩”,这一串词是《重走》第一章“长沙:和平的最后一瞥”题目下的关键词,每一章的正文开头,都有这样一串关键词。这是杨潇给读者划出的重点吗?
“我喜欢凡尔纳的小说,他的《神秘岛》就有这样的关键词,我这么写是模仿他,向他致敬。”杨潇在成为作家之前,是记者,“我列出有意思的关键词也是吸引读者阅读。西南联大的题材写得很多了,我这本书又比较长,我要想办法减少与读者间的鸿沟,尽量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些关键词还有一个拼贴的效果,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细节拼到一块,会引发好奇,我觉得现代写作或者现代性有部分是来自拼贴,因为现代生活是破碎的、琐碎的,拼贴起来会有一些渐离的效果。”
寻找当年的“东门”,重建历史时空
联大师生1938年西迁,杨潇2018年重走,他们踏上的是同一条路吗?
80年的间隔,从一条时间鸿沟,变成了一条空间通道,杨潇用脚丈量1600公里全程,带着史料与问题。在长沙,杨潇拜访联大师生乘船出发的码头,寻找张伯苓与蒋梦麟争吵的49标男生宿舍;在黔东青溪,找到了他们曾经下榻的天后宫,发掘了一座铁厂与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在黔中贵定,找到了接待过他们的大户人家的后代,听到了一个教人唏嘘的故事;最终他们一起到达昆明,在大观楼旁聆听梅贻琦与蒋梦麟的谈话。
玉屏,是重走路上进入贵州的第一个县城,杨潇说:“从长沙出发15天了,走到玉屏才第一次体会到‘重建’一座城池的趣味。”师生西行,大概都是从东门进入县城,杨潇就去找县城的东门。“我在玉屏只看到一条老的东门街,还有一点点当年的样子。”杨潇在城里寻找师生们住过的县署和孔庙,和当地大爷大妈们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他们的讲述和我阅读的日记、史料交织在一起,再稍稍用一点想象力,那些被拆毁的老房子就一排排立了起来,那些早已被‘下脚’(填作地基)的石头也一块块破土而出,城门、城墙像拔节的竹笋一样快速长高……”
跳跃、穿插、交织,《重走》构建起时空交叠的场景,很多时候杨潇本人也在里面。杨潇采访“联二代”赵新那,她的赵元任之女,看到一张照片,“我尤其留意到赵元任和家人友人们在沃克街27号那栋米黄色两层小楼——这栋房子离我2013年访美期间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数十米,在阳台上就能望见——楼前的几张合影,有一张是与胡适,他穿着黑色的大衣,左手提皮包,右手拿帽子,两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表情有点拘谨。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雪后初晴的波士顿,几乎可以嗅到空气里融雪剂的气味。”
杨潇说:“感性也是进入了历史的一种方式,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感性并不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它能帮助你调动更多感受触摸历史。”
《重走》2021年出版后,斩获多个文学奖项,杨潇在采访时表示,目前这部书已加印11次,销售十几万册,远超他的预期。一直有读者询问行走的意义,“1938年的湘黔滇旅行团,还是80年后我的重走,都有寻路的意义。”杨潇在书中说:“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同时,也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2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在《重走》的尾声部分,湘黔滇旅行团成员、已过百岁的吴大昌对杨潇回忆起一件往事。在2012年或者2013年,吴大昌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冯友兰论人生》,拿来翻一翻,有一篇叫《论悲观》,“这件事情我完全忘记了……哎,一看这篇我就起来了,这篇文章是为我写的。”
1939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的第二年,21岁的吴大昌陷入对“人生意义”的困惑中。他写信给冯友兰,冯友兰约他面谈,后来又写信给他,说自己写了一篇叫《论悲观》的文章,发表在《云南日报》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恐怕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冯友兰在那篇文章里写,“我们可以问: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但人生的整个,并不是人生中的事,而是自然界中的事,自然界中的事,是无所谓有目的的或无目的的,我们不能问:有人生‘所为何来’,犹之我们不能问:有西山‘所为何来’。”但这“没有意义”,并不等于不值得过,或者不值得做,因为人生“本身即是目的,并不是手段”。
杨潇采访吴大昌时,老先生已101岁,此时的他认为冯友兰说的是对的,“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